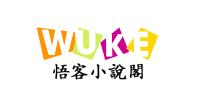『作惡』的手被容敬抓著,瑾萱瞅了瞅自己的手,又瞅了瞅容敬,臉瞬間垮了。
她說怎麼不疼呢?
老天又玩她是不是!
「我…」瑾萱扁了扁嘴,「我要說我掐錯了,你信嗎?
」
容敬嘴唇抿成了一條直線,在瑾萱看來仿若遊走在生氣的邊緣。
她心中叫苦不疊,自個兒怎麼就是有這種本事,她真沒想氣他來著。
「要如何,你說,我都聽你的。
」瑾萱小小聲地說道,她決定少說話,又怕容敬覺得她沒誠意,「我是真心想負責的。
」
說完便閉了嘴,多說多錯,在事態沒變的更嚴重之前,她盡量不開口。
容敬剛才差點破功,他著實想不明白,明明自己並沒有那麼多的情緒,為何瑾萱總能輕易挑動他的神經,在認識她之後,喜怒哀樂這些以前並不存在的情緒,都漸漸
變得清晰起來。
甚至…有了掛念。
容敬沉吟片刻,狀似有些傷腦筋。
靜靜等著『最後的宣判』,她不知容敬會不會輕輕放過,若是這般,她大概會很失望的吧。
瑾萱低著頭胡思亂想,不敢去看容敬。
她怕自己再犯錯誤,畢竟對上容敬,她總是憑著本能行事。
好吧,她承認,她就是垂涎容敬的美色。
不經意間,瑾萱舔了舔唇角,又想到剛剛『意外』的一吻,嘴角彎彎。
容敬的嘴唇,好軟呀。
就在她馬上又要傻樂出聲之時,便聽頭頂上容敬頗為無奈的說道,「既如此,那自明日起,便來府中伺候筆墨吧。
」
「伺候筆墨?
」瑾萱倏地擡起頭來。
「嗯。
」容敬闆著臉,點了點頭。
就…
隻是這樣?
瑾萱一雙大大的眼睛裡呈現出兩個字——失望。
「好吧,」瑾萱復又低下頭去,像洩了氣的皮球般,嘟囔了一句,「怎麼能這麼簡單。
」
「你說什麼?
」容敬沒聽清,隻瞧見了她嘴在動。
「呃,沒什麼,」沒想到被抓了包,瑾萱隨後仰著臉又問,「那要多久啊?
」
「直到我消氣為止。
」
「哦。
」瑾萱點了點頭,她說話算話,那無論什麼要求,她都照辦。
容敬不動聲色的將手收回,心間微微有些不舍,卻也知現在急不得,神色間滿是淡然,很正經地開口道,「我送你出去。
」
「好。
」瑾萱老老實實地走在容敬身側,半點麼蛾子也不敢出了。
直到被容敬送上轎後,瑾萱還在心裡糾結『就隻是伺候筆墨這麼簡單』『被佔了便宜難道不應該以身相許』之類的,她之前真的是滿懷期待啊。
現在這麼不痛不癢的放過她,她心裡可不是個滋味了。
站在一旁磨墨算什麼負責嘛,他處理公務…
等等!
瑾萱眼睛突然瞪的老大了,心裡止不住地『砰砰』直跳,彷彿要跳出嗓子眼一般。
容敬讓她入府司筆墨,那不就是說明日她又能來相府了?
!
而且,這算是真正地,容敬主動讓她來相府,不再是她自己一頭熱的往這跑了。
『咕咚』
瑾萱使勁咽了下口水,那是不是說明,他在處理公務時,她也能相伴左右?
倆人不再是單單地棋友了?
瑾萱捂住嘴尖叫了一聲,把轎夫嚇了一跳,「郡主,您怎麼了。
」
「沒你們的事。
」瑾萱話中帶著笑音兒,若不是轎中地兒太小,她都能蹦起來。
而相府大門外,一抹修長的身影依舊立在那裡,那雙眼睛此時正看著她離去的方向,目及遙望。
入府轎落,轎夫剛要去掀轎簾,便見郡主一陣風般從轎中跑了出去,一聲吩咐都沒有。
「頭兒?
」轎夫詫異的看向轎夫長,郡主這是怎了?
領頭的也疑惑,之前郡主在轎子裡叫來著,現在又一陣風地跑沒影了。
這是?
瞅了瞅還在晃動的轎簾,領頭的一把掀開,三百六十度無死角查看了一遍,啥東西都沒有啊。
「擡下去吧。
」他揮了揮手,郡主的心思他也猜不出來呀。
「誒。
」兩個轎夫將轎子擡走,轎夫長背著手搖著頭也離開了。
奇怪,奇怪啊…
不止轎夫們奇怪,近身伺候瑾萱的又怎麼樣?
雲兮四人可是見自家主子咧著嘴就回來了,一見她們便嘿嘿傻樂,連話都不說。
給雲兮四人嚇的,還以為她受什麼刺激了呢。
不僅如此,她們伺候瑾萱回房之後,瑾萱便坐在梳妝鏡前,一遍又一遍地照,邊照邊摸自個兒嘴角,那模樣就跟剛吃了什麼人進美味似得。
「主子,您怎麼了?
」竹瀝著實憋不住,主子太奇怪了,這段時間主子出入相府,已經正常多了呀,怎今兒成這樣了。
瑾萱倒也沒不理人,擺了擺手依舊樂呵呵的道,「沒事,你不懂。
」
不懂?
竹瀝眨了眨眼,主子高興地事這麼高深莫測嗎?
「主子,喝茶。
」雲兮端了茶來。
往日瑾萱的習慣,回院後先飲茶,歇口氣再乾別的。
但今日不同,瑾萱瞅著茶盞直搖頭,看著茶仿若看著什麼似的,猶豫半晌忽然眼睛一亮,「去給我拿個蘆管來。
」
「啊?
」雲兮蒙了。
「快去。
」
「哎。
」
雲兮納悶地去拿東西,瑾萱則晃了晃腦袋,她覺得自己還是很機智的嘛。
唔,今日她這張嘴啊,可不能蹭著了。
一直到晚上歇下,瑾萱當真吃了一天的流食,不管是啥,若是不能用蘆管進,她就不吃了。
雲兮四人直到睡下都沒鬧懂,今日主子到底是怎麼了。
夜晚,躺在床上瑾萱覺得自己就像做夢一般,她蒙在被子裡偷偷的笑,往後她再也不用費腦子想法子去找容敬了。
唔,另外她得想想辦法,讓容敬心裡的氣存的長長久久的才好。
這樣,她就能一直待在他身旁了。
瑾萱一會傻呼呼的笑、一會又笑的甜蜜,總之一晚上沒個消停,弄得在外值夜的竹瀝愁了一晚上。
小姑娘支著下巴坐在榻上思考,這些日子主子除了去相府哪也沒去,丞相夫人病了,她家主子一直侍疾來著。
想來,自家主子何時做過伺候人的活計,若不是對容大少爺真心愛慕,主子如何能放下身段去做這些事情而毫無怨言。
那今日這個狀態,肯定也和相府,不,是相府大少爺脫不了乾係了唄。
竹瀝嘆了口氣,無奈的看著那被幔帳遮住的床榻,就不能給她個痛快?
主子到底為何這樣,誰來告訴她啊!